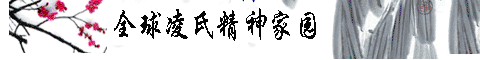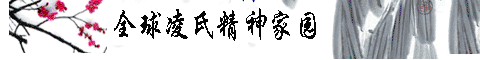|
各位尊敬的读者好!小马的这篇小说比较特别,是采取类似口述的方式来写的,感情戏很多。
如果阁下喜欢很多打斗场面,而且要章章精彩的话,恐怕这小说会令你失望。同时如果阁下喜欢看轻松喜剧,不想心情变得太沉重的话,也请您不用看下去了。因为虽然这小说有不少喜剧的成份,但更多的是悲伤,我不想令您的心情变坏。
小马在构思这小说时,曾几乎眼泪要掉出来,这是写作以来的第一次。
不过那毕竟是我的个人感受而已,我对感情戏的写法比较陌生,能不能把那些情感写出来,那就有待各位读者评定了。
※ ※ ※
我,凌峰,公元2075年3月24日生,地点是亚洲东方某某大城市的一家小医院里。
许多人都以为我出身于军人的家族,听起来就好笑,他们怎么会认为一个将军就一定要生长在军人的家里?遗传这东西,只会传外形,不会传内里的。豪门多败子,这难道他们没听过吗?
其实我的家很穷,那穷困的地步许多人都想象不到。“家徒四壁”这成语,用以形容我们家,倒是十分贴切。
家里实在没钱,连母亲生下我之前都没有去医院检查,从而造成了一个悲剧…唉,一想起这些久远的事,我的心情还是会很低落。
父亲说过,其实他一直催着母亲去看医生,但母亲不舍得那区区的看病费,又想到楼上楼下有几家都是这样将子女生下来,也就没有去医院了。
其实谁都不知道,我母亲盘骨太小,而且在腹中的我有严重的错位,不宜直接分娩。本来这些都可以在产前发现并纠正,但我们那贫民窑的习惯,是找个助产妇帮忙生下就算,所以直到了临盘的那一天,那楼上的大胖婆瞪着我露出的一只小脚,手足无措,父亲才知道问题大了。
父亲说,送医院的途中,他看见母亲体下的血巴巴地流下来,整个人苍白得象张纸,他的心比谁都难过。
他记得,母亲最后和他说的一句,是叫他尽力养育好我,让我能和父亲一样有骨气,最终出人头地。
父亲当时就大声喊:“我错了!我脾气不该这么硬,当初如果我不娶你,你就不会和我挨穷,都是我害了你!”
可无论他怎么叫,母亲还是晕过去,然后再也没有醒来。
在医院里,医生们花了三个小时,将母亲的肚子切开,把一动不动的我取出并救活,才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。
可我由于脑部缺氧达三十秒之久,因此大脑皮层受到一些损伤,天生就有些痴呆,而我的左手总是在颤抖,怎么样也停不住它。
我时常在想,如果母亲没有怀我,可能就不会死,家里也不会弄得这么穷。我是否真的是个“祸胎”,本不应出现在这世上?这问题常常困绕着我,直到长大。
医院的帐单经过政府的扶贫基金减扣后,数目还是不少,而且母亲的敛葬,又花了一大笔钱,父亲为了这些花费,不知举了多少债。
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光蛋,再加上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,可想而知那日子有多么难过了。
幸好还有我奶奶帮忙,她在家里开了个小小的幼儿园,看管我和几位父亲的穷工友的儿女,将得到的一点微薄收入,勉强可以用来给我买奶粉吃。
父亲的那点工资,几乎全用在还债上,而奇怪的是,他越还就越多债务缠着他,据奶奶说,有一段时间,每天晚上都有人半夜敲门要他还债,还在墙上画了各种可怕的字样,弄得周围人心惶惶,小小的幼儿园被迫中止了几个月。
当我两岁时,有一个债主终于忍耐不住,冲进我家,将我一把从奶奶怀里抢走,临走前威胁奶奶说若不还债,就会对我不利。
奶奶跑到父亲的工厂里,第一时间将这事告诉给父亲,他们不敢报警,但又没有钱可以还。
奶奶说,父亲后来冲出了工厂,不知上哪儿去了。晚上时,我就给父亲领回了宿舍。
她追问父亲怎么回事,父亲沉着脸不说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不过后来奶奶时不时会在年幼的我面前唠叨这事,还问我:“小峰峰啊,你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救你的吗?”
我只会傻乎乎地望着她,因为我也根本不知道。
自那以后,债主们一个接一个消失,可能他们终于意识到我们榨不出什么油来,只好自认倒霉,不再天天上门催交欠债了。
我奶奶很疼我,常常抱着我轻轻地摇,哼哼地唱着什么歌谣,而我都会很乖地睡在她怀里,不会象其他小孩一样吵吵嚷嚷,令她头痛。
她知道我脑袋受过损伤,天生就很笨,所以也很有耐心地教我,不会轻易放弃。
据父亲说,最初她为了让我能见到汤匙,自动张口吃稀饭,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,天天重复地将我的口叉开,然后将汤匙放进口里。
我到了两岁时,才终于学会叫一声“奶奶”,那天奶奶开心得象中了头奖,一个月都笑吟吟地。
在三岁时我才学会怎么走路,往往是迈开两步,就又摔倒。令奶奶和父亲都十分担忧又心疼,真不知以后我将会如何适应这个快节奏的社会。
我父亲尤其担心,他那时常常对奶奶说,小峰这么笨,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他怕不能做到母亲交托他的任务,我到最后只能步他的后尘,甚至比他还要差。
奶奶就会安慰他,说上天总是公平的,他某些地方有缺陷,可能在其他地方就有补偿。只要我们尽了力去教他,他还是会有前途和希望的。
父亲听了后就会不出声,一直看着我,而我也会看着他,我奶奶说,有时候我们父子俩会这样对望一个晚上。他会对我笑笑,拍拍我的头,我会张着口,侧着脸瞧他,一副傻乎乎的模样,甚至还会哭起来。那时父亲就会把我抱起,一边上下晃动,一边望着天花板,咬着嘴唇。
直到有一天,奶奶见到一件奇怪的事,才证实了她说过的话果然不假。
一只不知死活的老鼠,被隔壁的花猫追得走投无路,冲进了我们家的门。
花猫也跟着窜进来,撞到奶奶的脚上,把她给吓了一跳。
小小幼儿园里的其余三名小孩,都尖叫着四散走避,偏偏好象老鼠走到哪儿,他们就跑到哪儿去。
于是那老鼠就跳到床上,想要经过窗口逃走。
结果奶奶就看见还扎着尿布的我往前一扑,将那倒霉的老鼠压在掌下,那动作快得很,按奶奶的说法:“你本来和往常一样,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,其余孩子怎么逗你,你都不动。可那一下,真比那只猫还要快三分,把我的心都给吓得跳出来了!”
然后,奶奶就尖叫一声“天呐!我的小峰峰,你在干什么啊!”她赶忙走上前要扶起我,可见到我手下的耗子在吱吱地叫,却本能地退缩了。
奶奶怕老鼠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。她的解释是:“如果你试过晚上睡觉时被耗子咬去半边耳朵,你也会怕这些该死的小畜生的。”当然,我是“初生婴儿不怕鼠”,只把那可怜的它当作一件玩具,当然没有任何恐惧了。
那花猫犹犹豫豫地走进来,看着我手底下的老鼠,“喵喵”地叫了几声。
接着,奶奶就惊讶地看见我把老鼠拿起,递向那只猫。
看见老鼠在我小小的手中挣扎,花猫就好象看到精美点心一样,忍不住凑过头来要咬。
这时奶奶终于壮起胆,手掌一拍,将那耗子从我掌心打落到地上,花猫头缩了一缩,接着立刻叼起地上的小老鼠,飞也似地跑了。
奶奶连忙将我的双手洗了又洗,一边还嚷:“哎呀,我的小峰峰。你怎么学起抓老鼠起来了?这怎么得了?这怎么得了……”
晚上,当她将这件奇怪的事告诉给父亲时,父亲还不敢相信。
“他平时连路都走不好,怎么可能捉得住老鼠?”父亲揉着通红的眼睛道。
“唉,你连我的话都不信么?你看看,我还特意把那床单保留下来,你看…”
果然,父亲看见发黄的床单中间,有一块黑色的斑点,上面有几条鼠毛,这才明白确有其事。
他带有疑虑地望望我,跟奶奶说:“难道他上辈子是只猫,所以这辈子还记得怎么抓老鼠吗?”
奶奶说:“是啊,我也有这样的怀疑。咱们的小峰峰还会听猫讲话呢,那花猫叫了两声,他就把老鼠递给它,真象懂‘猫语’的样子啊!”
父亲笑了:“妈,我是开玩笑的。你不要疑神疑鬼,想偏了。峰峰怎么会懂猫的话呢?可能那是凑巧罢了。”
奶奶就说:“那是我亲眼看到的,你怎么就不信呢?”
父亲还是在笑:“可那真的是不可能的。”
奶奶只好负气道:“好了好了,那是我眼花,看错了,行了吗?”
于是父亲转头看着我,又对我笑着说:“峰峰好厉害!逮着一只大老鼠。YEAH!!”他抱起我来,原地转了两个圈。
然后他呆住了,因为他发现我在笑。
那可是我第一次对父亲露出笑容。
……(沉默十秒钟)
其实这件小事,说穿了也没有什么,不知从婴儿的什么时候起,我就能感受别人的心灵,模模糊糊地知道他的内心是开心还是烦恼,还能知道一些思想的片断。
或许我对动物感觉更加敏感,因此那时候我知道花猫要抓那只老鼠,就出手帮了它的忙。
而我两年来一直不能对父亲笑,可能也是因为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悲哀吧!
我的左手虽然还是一直在颤抖,可我的动作并不比别人慢,相反,有时候我可以快得连自己都不相信。
父亲直到我五岁时,才真正相信我的特殊能力。他很慨叹地说,上帝真的是很公平,他夺去了我的智商,却给予了我阅人的智慧;他让我左手永远颤抖,但又使我动作灵敏。奶奶则说,那是我母亲和爷爷在天保佑我们的结果。
可能上帝还是公平的,他少给你一些东西,然后在另一方面,他会补偿给你。至于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安排,那他就不管了。
…
四岁的时候,我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出房门,见识到外面的世界,而原来在小小幼儿园的朋友一早就到处乱跑,和宿舍大楼的人都混熟了。
他们见到我出来,就拉着我到处串门,大楼里面都是我父亲的熟人,大部分都知道有我这个呆子。见了面,他们会问长问短,见我结结巴巴地回答,他们除了叹气,还是叹气。我则会眼直直地望着他们,一声不坑,直到他们打发我走为止。
我那时才渐渐知道,原来一个家庭里,除了父亲和奶奶外,还应该有个母亲和爷爷。于是我问奶奶,他们在哪儿呢?
奶奶指着天上说,他们住在上面,一个叫“天堂”的地方,非常地快乐。
我问,为什么他们不和我们一起住?
奶奶抹抹眼,说以后会的,以后一定会再和他们相遇的。
于是我也不再问什么,只盼望相遇的那天早日到来。
我只在相片上见过我的母亲。她的笑容甜甜的,和父亲很合衬。相片里两人紧紧靠在一起,看了让人觉得很温暖。除此之外,我只能依靠幻想,来想象如果见到了母亲,那将会怎么样。
我常常梦到和母亲一起玩耍,一起唱歌跳舞。累了的时候,她会抱着我,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。可我总听不清她的话,甚至她的面容,在梦里也显得十分模糊。没办法,我很想念她,可见不了她…
唉,不说这些了,每次提起来,我都很难受。还是说说其它的吧!
我父亲做的是一家电子工厂的装配工作,据他说,只要把什么和什么拼在一快,然后用焊枪固定好就行,听上去很简单,但如果要一天做上五六百件,就很繁重了。
那一行虽然容易,但工资低,危险度又高,我就亲眼见过他被焊枪烧伤的手,手指上黑了一片,十分吓人。但父亲说,那工厂能一直请工人,而没有用机器人来替代,已经是很难得了,所以即使有点危险,也得做下去。
我们住的是工厂临时搭的钢架房子,共有五层,三百多户和我们差不多一样穷的家庭住在一起。
这种房子冬冷夏热,而且每一层只有四个厕所和四个洗澡间,六十多户人都得分着用厕所,经常出现外面几个急得要命的人在拍打厕所门板的场面。
我小孩子开始时最随便,找个阴暗的角落就撒上了。不过有次我被个叫“卫生巡检员”的家伙抓到,被罚了一千块,父亲虽然没有打骂我,可我知道他几个月省下来的钱又没了,于是以后就再也不敢这样做。
别人都说我笨,可有些事我还是很清楚的。
还好,这宿舍大楼总算铺了自来水管。不用和别人争水,只是到了冬天的时候,水管都结了冰,那我们得拎着铁桶去附近的消防水龙头排队打水。那时我们会呵着冷气,和前后的熟人颤抖着谈天,说到后来,连舌头都会冻得打结,话听起来含糊不清的。
也是在那时,我开始认识张前。
张前和我年纪相同,都是75年出生的,人长得削瘦,脸好象三角形,有人称他“小狐狸”,看上去倒真的有点象。
他经常正好排在我后面,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,而往往都是他说一大堆东西,听得我糊里糊涂的。
用铁桶打了水后,他经常会问我:“呆子,你能不能做点好事,帮我将这桶水提上我家?”
我说:“好啊!”就左手挽起他的水桶,右手提着我的铁桶,将两桶水同时提上一层又一层。
他会在旁边给我打气:“好!继续,凌呆子你是行的!”
我知道他心里其实在嘲笑我,不过我习惯了,也毫不介意。
工厂宿舍的几个主妇,刚见这场面时,还会过来训斥一下张前,可后来就慢慢见怪不怪了,甚至她们也开始叫我帮手。
“小峰,帮我提桶水来好不好?阿姨给你糖吃。”一位主妇叫。
“好!”我立刻去办。
“凌呆子,楞着干什么?快帮我搬煤气瓶!”这个更不客气。
“来了!”我马上跑去,提起煤气瓶的另一端,一大一小合力将瓶子提上楼梯。
仅仅五岁的我,可能就是这些事情做得太多,从那时起,我的身体就一直很壮,胳膊和手腕比一般的小孩要粗。
张前也跟我混熟了。见到面,他会一把捉住我肩头:“凌呆子,来,跟我去外面玩。”
“可是,我还没给李大婶打好水呢!”我提起一个空水桶。
张前从我手上夺过水桶,跑上楼去,将水桶扔在李大婶门前,回来对我说:“你这个呆子,光会帮别人,不想想自己。这样做,迟早整个宿舍的水都要你一个人来提。你不累死才怪!”
我张大了口:“累死?那是什么意思?”
“唉……”张前不耐烦地叹口气,“那就是做事情太多,上了天堂,见江泽民去了。”
“啊?!”我有点惊讶,“上天堂?那太好了!我不就可以见到我妈妈了吗?”
“唉……”张前摇头又叹气,“这个呆子,真没救!算了,你以后还是跟着我好一点,免得受人欺负。”
回想起来,我真不知五岁的张前怎么会这么早熟。可能这和他也生长在单亲家庭有关吧。
于是张前经常带着我到处去,两个野孩子就疯疯颠颠地到处捣乱。
张前知道的好地方很多。有地质局,有高级医院,有著名大学,还有全市五个大公园,十几个小公园,他都了如指掌。
他最爱去的地方,是十几条街外的一所大学。那大学的环境干净舒适,高大的现代化教学大楼,还有些园林建筑,和我们所住的贫民窑真是一个天,一个地。
大学的门口有警卫,有摄像机,又有刷卡的机器,普通小孩子根本进不去。但张前总能找到一些漏洞,或者是一处排水渠,或者是一棵过墙的老树,又或者是一扇无人看管的铁丝门,他总有办法可以溜进去。
而我则傻乎乎地跟着他做这做那。
…
我印象最深刻的事,发生在几个月后,夏季的某一天,地点是那大学的某处墙外。
“爬上去,凌呆子!”他指着这两米高的墙。
我一跳,捉住墙边的装饰,三两下就攀上了顶。张前很清楚我的能力,爬不上的地方,他不会叫我尝试。
“有没有摄像机?”他在下面小声地问。
我看了看四周:“没有。”
“绳子。”他对我点了点头。
我把捡来的一根纤维缆绑在墙头,他就顺着这缆绳一点点慢慢往上爬,最后我还得扯他上来。
张前一上墙头就笑:“哈哈!今天我们由正门走出去,气死那个守门的家伙。”
一进大学,他就如鱼得水,尽情地放纵。
我们先去一个室内运动馆,张前说到下午两点以前,那里都是空的。
果然,我们由地下室的窗口钻进去后,见到里面空荡荡的,没有半个人影。
于是我们把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扔得到处都是,还从跳马上做个凌空动作,翻身掉到下面的软垫上,将雪白的帆布踩出一个个小鞋印。
“嗨!”他一个鹞子翻身,在空中转了一圈,屁股落在垫子上。
我做的空翻动作比他要夸张许多,是在空中翻了三个筋斗,然后稳稳地落到软垫上,把他给看得目瞪口呆。
于是,他也不甘示弱,学我那样翻身下落,可都摔了几次四脚朝天。
他很气愤,对我大喊:“你再做一次!”
我感觉到他并不想我做,但既然说了出来,于是我就又爬上跳马,重复了刚才的跳跃。
又是三个筋斗,又是双脚落垫上,一丝不差。
他的样子,看上去惊讶多于生气,但还是叫:“再来!”
我摇了摇头。
“怎么?你不敢了?”他满脸挑衅。
“你准备要趁我爬上去时推我下来,那我为什么还要跳呢?”我很不理解他的想法。
“什么?”他好象被针刺到一样窜起来,“你说什么?”
“我…”我突然想到父亲反复交代的话,千万不要让人知道自己有洞察人心的能力,所以就闭口不说,任由他的手指对着我脸。
他看上去很激动,手指在我眼前发抖:“你不是呆子,你是个疯子,专说疯话!对,你名字叫峰,本来就是个疯子!哈哈!”说完,他扬长而去,而我则紧跟着他。
我想,当下一个体育课的老师发现运动馆内乱七八糟,软垫被印上几十个黑乎乎的小鞋印时,一定会气疯了吧!我当时并没有想这样做是错还是对,只知道要跟着张前这里去,那里去而已。
不过说真话,和这调皮的张前在一块,其实我也是乐在其中的。
我们的下一站,是一栋大楼的顶层,那里全是空课室,我们互掷书写笔,把那些笔摔得辟里啪啦地闪着电光。然后又乱按那些电子投影器的按钮,看着一个个立体影像在面前交叉杂乱地显示,我们开心得拍手。
一个蓝色的大圆球出现在眼前,上面有颜色深浅的几块硬壳覆盖,外面有白色的一层薄薄的雾,还在慢慢地转动。
我问张前:“这是什么?”
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,说:“你这笨蛋当然不知道了。这是大气球,充了气就会往天上飞。我以前在公园里见过呢!”说完,头高高地翘起,一副很了不起的模样。
我不禁衷心地说:“哇!你知道的真多!”
“哼!那当然了。”他叉着腰走到讲台上,对下面坐在课桌的我说:
“别人都说我一辈子都进不了这学校。真是@#$%&*(粗得很,省略)……你看着,总有一天,我会站在这里,给所有看不起我的混蛋讲讲课。”
“好啊,好啊!”我下意识地附和他,拍着掌。
“嗯……很好!”他尖尖的三角脸露出笑容,看来很开心,又说:
“今天我心情特别好,就特许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吧!”
哈哈,可能任谁都想不到,我的童年是那么调皮捣蛋的吧?虽然我是被动的,但如果没有这段打破常规,疯疯颠颠的日子,可能往后我也只是循规蹈矩,不会做出一些别人难以想象的事来。
好了,说了这么多,可能你们会嫌我老头子罗唆吧?如果还感兴趣的话,那请明天再听听我其余的故事。
好,那就暂时再见吧!
好了,停住吧!不要再记了。
呵呵呵!怎么连这个也写下来了?停止!STOP!
咦?怎么还不行?凌丽,小丽,快过来帮帮我。
爷爷,什么事呀?
这个电子日记关不了,一直在记录,你看,又打上去了。
按这个钮不就得了?
噢…
|